|
《走錯路》 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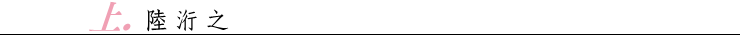 |
| |
「陸洐之,你真不是東西。」
一個剛跟他在床上翻雲覆雨過的炮友如此道,陸洐之沒生氣,反倒覺得好笑。
「我本來就不是東西。」
那人:「?」
陸洐之看都不看他。「我是人,不是東西。」
那人扯了扯唇。「好吧,你不是人。」
陸洐之挑眉。「我記得沒錯的話,你剛剛被我這『不是人』搞到射了三次?所以你的嗜好是人獸交?」
那人:「……我不跟你說了。」跟律師辯嘴,還真沒啥贏的可能性。
陸洐之依舊不動聲色,穿戴好了衣物,將袖釦一一別好,那人看得很神奇。「你都不問我一下何出此言?」
無聊。「何出此言?」
那人:「聽說你甩了小岩?」
陸洐之嘆口氣:「我沒甩他。」
那人:「?」
「我只是拒絕他,然後選了你上床。」
陸洐之口氣一副就事論事,那人笑了。「是啊,當著人家面,攬過我的腰,然後說『我對你膩了,技術練熟點再來』,承蒙你如此瞧得起我。」那人道:「小岩都哭了,他才剛進圈而已,據說你是他的……第二個?」
陸洐之:「所以我是為他好。」男人穿好西裝外套,轉身走了。
陸洐之對自己童年的記憶很模糊。
人類都有所謂的趨吉避凶心理,有些事,太不愉快的,不想記憶,抹煞著抹煞著,就淡掉了,唯獨對某些細節會有本能的厭惡殘留,其中之一,陸洐之特別討厭看人軟弱。
那會令他聯想到幼時無能為力,被人排擠欺負的自己。
所以在圈子裡,倘若遇到太弱兮兮的對象,他總格外厭煩,通常都會用不大客氣的態度。
反正這輩子,情情愛愛的,打一開始就被他挑開至人生目標以外。
他沒受過這方面的傷害與折騰,純粹是沒有興趣而已。
或者說,天生同志的他,事業與感情線勢必無法畫上等號,從政是他的理想,台灣的政治圈……不,全世界都一樣,沒一個地方會完全接納同志成為領導,他沒有任何譴責意思,純粹闡述現狀,於是他也選擇得很快:太虛無縹緲的東西,他不需要。
他不想再歷經一次,彷若小時那般的徬徨無助。
第一次見到喬可南的時候,是個冬天。
寒流來了,天氣很冷,他從小體溫偏低,大抵沒受過好的照顧,即便長大後極力健身,手腳冰冷的毛病還是擺脫不掉。
事務所介紹新進人員,他沒興趣,但仍義務出席,站在牆角,他手凍得要命,插在口袋裡仍有絲絲涼氣,滲入腿膚,每到這時他總懷疑人類怎能有這般低冷的體溫。
他臉色很差,只想結束了工作,找個人擁抱。
「我是喬可南,大家可以叫我Joke。」
很乾淨清朗的男聲,不算太低,也不算高。
喬可南?Joke男?
這名字太喜感了,導致陸洐之抬了抬眉,瞥向青年所在位置,目光一震。
濃眉大眼。
這是陸洐之對喬可南的第一印象。
那黑黝黝的眼,亮澄無比,眉毛微揚,形狀是很自然的精神好看。
第二印象是……他笑得真好,嘴唇微翹,幾顆白玉似的牙在唇縫間隱約露出,黝黑色的膚很是健康,整個人透著一股暖烘烘的氣息,彷彿能教人感受到陽光。
陸洐之手腳瞬間就沒那麼冷了,微微的熱從他腳根底隱約湧上,匯聚在下腹處──
那是一個男人最原始本能的反應,在面對他有興趣的人物時,野蠻又直接,倘若這是在Gay Bar裡,他定要用盡渾身解數,得了這人,甚至或許等不及開房,隨處找了個僻靜地方,就要開幹。
但,現在不是在Gay Bar,而是在事務所裡。
他平時工作的地方。
所以陸洐之很快按捺下了那股莫名所以的衝動。
他的手腳,又逐漸恢復了冰冷。
當晚他就去了Gay Bar,這次挑了一個膚色較深,身形結實,五官俊朗的。
這晚他幹得很是痛快,轉眼就把對喬可南產生的不明衝動,拋諸腦後。
據說Gay跟Gay之間都會有個雷達,嗶嗶嗶,準得很,陸洐之的開關大約是壞掉了,或者他從沒開啟打算,最好他察覺不到別人,別人也覺察不到他。
糜爛幾晚過後他就把喬可南忘了,本來這世上就不是真的缺誰不可。
倒是喬可南在事務所裡很受歡迎,雖有點兒呆呆傻傻,其實待人接物,很是機敏,會看人臉色,遞茶端水,時機態度,恰到好處。
據說是因他高中時失去父母,在親戚家借住一陣的關係,但青年臉上倒是看不見那種依附人的諂媚,反而像是做得習慣了,而他也不討厭這麼對人。
略微相似的遭遇,但塑造出來的人格,卻是兩樣的大不同。
陸洐之扯嘴哼笑。
日子就這麼不鹹不淡地過,冬天過去了,春天來臨,隨著季節入夏,陸洐之體內那股騷動也漸漸地沉寂了一些。台灣的夏天很熱很悶,但總比冬天又濕又冷,手腳如冰棍般暖不起來的好。
助理辦事去了,陸洐之起身,給自己倒茶。
外人說他難搞,卻從沒人講他擺架子,因為他連茶水都會自己倒──儘管大部分時候實在忙透了,索性不喝,渴一下午,連廁所都免上,導致那陣子他嘴唇皸裂得厲害,挑了好幾個牌子,才挑到不那麼油亮,又適合他情況的護唇膏。
他走到茶水間,不意撞見裡頭的一個人影。
那人像是剛跑外務回來,外套脫了,襯衫袖子拉至手肘,襟口微開,他仰頭喝水,一點水液從他嘴角邊滲落,淌過他起伏的喉結。
大抵在辦公室久了,青年原先黝黑的膚色漸漸褪至淺白,如象牙一般,坦露的肌理線條仍舊結實,卻又帶點柔軟。他頭髮長了,微遮住眼……那雙黑澄澄的眼,欲遮還露,吸力不減。
陸洐之幾乎看得傻了。
青年一愣,停下喝水動作,瞥頭看見陸洐之,展顏微笑。「啊,陸律師,來泡茶嗎?」
陸洐之一般懶得回答,要不他來茶水間幹麼?
可他卻破天荒地應了一聲:「嗯。」
「喝咖啡吧?」喬可南眉目彎彎,笑得那般舒心。說罷他動作,操作咖啡機,不一會兒咖啡濃郁的香氣充斥一室,他沒給陸洐之添加任何多餘配料,單單一杯黑咖啡,遞給他。「我記得您是喝這口味的。」
陸洐之微愣。
咖啡機是國外進口的,上頭好幾個按鍵,可以做美式、卡布奇諾、有的沒的,陸洐之鍾愛純粹不摻奶糖的黑咖啡,有時就連助理都會搞錯,他沒想喬可南居然知道。
喬可南笑了笑,「我聽小玫提過,她說她每次弄錯,您都會自己出來用。」害人家小姑娘很不好意思,這比直接斥責還丟人。
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」喬可南頷首示意,陸洐之點點頭,在那人擦過自己身畔之際,陸洐之彷彿嗅聞到那股屬於陽光的芬芳。
陽光是怎樣的味道?選一天晴朗日子,把堆積已久的棉被拿去曬一曬,下午收回時撲在上頭聞聞,就曉得了。
幸福得簡直能讓人落淚。
從這天開始,陸洐之挑人上床的口味又變了。
變得愛找膚色白潤、四肢修長、肌理堅實的陽光男孩,有些人甚至把自己弄成先前他喜好的那樣,結果人家魔術師,如今看都不看。
夏天過去,在還沒享受完秋季的舒和涼爽前,冬天就來了。
冬天是陸洐之每年最難挨的時分,他其實不怕冷,哪個冰棒怕住在冷凍庫裡的?但手腳冰冷,實在難受,每到這時他的糜爛程度就會大幅上升,在各種各樣的雙人床上流連、輾轉取暖,挨著浮木,度過漫長的冰河時期。
直到聖誕節,他在酒吧裡,罕見的放浪形骸,陸洐之雖性事上從不克制,卻仍有一定分寸,獨獨那次,他喝到爛醉,幾乎想不起自己前一晚幹了什麼,只知一個又一個的肉體疊了上來,分不清誰是誰……
自發的性愛跟被人當作性具感受差異極大,導致他隔天上班,臉色不好,宿醉加縱慾,只有糟透了三個字形容。
偏偏,還有個傻小子來觸他逆鱗,「陸律師,要不要吃糖?手工做的……」
喬可南沒講來源,但滿臉喜色,掩藏不住,顯見跟女友過了一個相當甜蜜的節慶,這令陸洐之心頭微微一刺,近乎憤世嫉俗的厭惡感油然湧上。他陰冷道:「你就沒別的事可做了嗎?」
喬可南嚇著了,搔了搔頭,說著抱歉,就出去了。
陸洐之毫無道理地想:你不知我不吃甜?
這想法簡直蠻橫至極,把自己當世界中心在轉,連陸洐之都想唾棄自己。
他冷靜下來,想想自己早上的表現,實在很難看,又無法放下身段去道歉,那人肯定覺得很討厭吧?
……越想越頭疼,陸洐之想給自己倒杯熱水,緩解一下,不料一走出辦公室,青年迎面而來,「陸律師你宿醉對吧?我這兒有解酒藥,你吃一片,會舒服一些。」
……
陸洐之這輩子從沒對一件事感到沒轍過,唯獨這人一笑,他便整個人手腳發麻,若不是長年ㄍㄧㄥ出的堅硬外殼,他真不知自己會化到何種地步。他是冰,冰怕熱,碰熱就要融化,灘為一地,最終蒸發,不復存在。
可他還是不自禁地,被那股熱暖吸引。
這不是愛,喬可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是那樣的。
陸洐之想了很久,直到有天看到助理小玫的鑰匙圈,是個很奇異的貓腳形狀,見她不時捏捏揉揉,他問:「那是什麼?」
小玫:「喔,這是一種治癒玩具,偶爾捏捏,紓壓放鬆。」
原來如此。
他想,喬可南對他的意義,大抵就是這個了。
他可以不擁有,就擱在身邊,看一看、捏一捏,就好。
助理小玫懷孕了,決定離職,安心養胎。
宇文博問他:「你要另外找人?還是調誰過去?」
陸洐之只想了一秒。「讓喬可南過來我這邊學習吧。」
宇文博一開始有點兒微詞,後來同意。
在喬可南進他辦公室的那天,陸洐之穿的是自己最好的一套西裝,袖釦是寶藍色的,太過奢華,他極少在戴,今次卻用了上。
喬可南捧著一盒自己的物品進來,他笑了笑,「陸律師,往後請多指教。」
陸洐之淡淡地「嗯」了一聲,好似沒太多關注,無人知道他其實連一個翻閱紙張的動作,都在腦裡先進行了十遍百遍。
喬可南個性是真的好,小玫已是在他身邊較久的助理,卻仍有處不來的時候,青年做事能力未必比人家優秀,但勝在心細、肯學,隨後他考上了執照,去律訓的那一個月期間,對所有暫時與陸洐之合作的人來講,不啻為一場惡夢──
他們甚至懷疑自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……即便成了屍首,陸大律師還是會拖著他們出來鞭屍。
導致喬可南歸來,受到的是全事務所有如英雄凱旋般的高規格接待。
陸洐之覺得自己跟青年的關係就是這樣了。良好的共事,喬可南也是真心仰賴他,儘管自己是同性戀,不代表非得和天下所有看得過眼的男人湊一腿,直到朋友很婉轉地聯繫,問他:「我這兒有一個人,你有沒興趣?」
簡直拉皮條的口氣,陸洐之哼道:「賣淫犯法。」
「誰跟你賣淫?」對方也是個律師,不過是個直的,有女朋友,提這事時口氣還很不自在。「就我女友的舅舅的男友的堂弟,認識一個人,對方挺安全的,說是被以前交往的男友劈腿甩了,因為那方面合不來……呃……我也是被人請託,聽說你有個很厲害的名號?」
陸洐之:「?」他對圈內人如何評價不感興趣,倒是第一次被用這麼正規的管道找上,莫非這事也有口碑的?
「我不喜歡死纏爛打。」
「喔,放心,對方不是那種人。我把他照片傳給你,考慮考慮。」
真成皮條了。陸洐之哭笑不得,收了信,先處置了一些工作再看,檔案一打開,他幾乎被嗆著,「喬可南?!」
照片裡確確實實是青年微笑的樣子,約莫拍了一段時日,樣子跟陸洐之最初看到他時落差無幾,男人反覆打開那封信和檔案,看著寄件人,是朋友沒錯,他回信:「你沒寄錯照片?」
對方回道:「沒,不過我也只有這張。」
這張就夠了。
陸洐之當晚真是翻來覆去,爬起身連抽了好幾根菸,他萬萬沒料到喬可南居然是同類,更沒料到他被人劈腿,還是因為那般可悲緣由,再沒料到……他居然託人找他幫忙開苞?
什麼跟什麼。
隔天陸洐之頂著眼圈上班,心思紊亂,喬可南到底知不知道那是他?結果一進辦公室,青年便朝他一笑,「陸律師,早。」
那一笑,跟往常幾無不同,青年還是那般純粹的樣子,陸洐之想:他應該不知道。
他煩惱了一下午,決定回絕,能當喬可南的第一人,他不可能不動心,問題兩人的關係太複雜了,職場上下屬,又是同性戀,扯在一起準沒好事。
他拒絕的信都擬好了,一直擱在草稿匣裡,只差按下傳送,然在看見喬可南無意識咬筆的當下,陸洐之把那封信刪了。
連同垃圾桶,一併清空,清潔溜溜。
有些事就是這樣,你不想的時候不會聯想到那方面去,一想……就沒完沒了。
他不是第一次對喬可南勃起,這是第二次,而他不想再找替代品,眼前是最好的人選,既是對方送上門,他沒道理不好好享用一次。
就一次,一次就好。
酒吧裡,喬可南發現是他以後,極度慌張,那種虛弱辯解的樣子撩起了男人的施虐慾,實在很想把這人幹得只能哭泣,哀哀告饒,他帶他去了最好的Motel,喬可南雖然跟來了,態度上卻顯露猶豫,陸洐之不逼他,只問了一字:「怎?」
「……沒事。」喬可南像是下了決心,再無疑慮,陸洐之很滿意。
他這輩子從沒擁抱過陽光,原來冰融化的滋味是這般,若不是記著對方是第一次,而他又堅決不想給青年造成任何不快,陸洐之當真會失控。
過程裡喬可南幾乎算是配合,毫無扭捏,偶爾害羞的樣子很可愛,教人很想看他更多反應,以初次的零號來講,喬可南表現可圈可點,陸洐之差點迷亂在他身體裡,尤其想到跟自己說過的僅只一次,那真是……
肉體之間的吸引力能有多強烈?那真是嘗受過的人才懂。
他以前遇過很多例子,離婚的夫妻,卻仍維持床笫關係,旁人聽來不可思議,他倒是很能領會。
尤其此刻。
陸洐之十分克制,只做了一次,就算喬可南身體柔韌度再強,初經人事,不宜一口氣承接太多。
走前他猶豫數回,終於開口:「往後……」
喬可南一向懂事,在這時也不例外。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他說得乾脆直接,臉上毫無不快,陸洐之笑了笑,撫過他的髮。
那柔軟細緻的感觸,直到他手握方向盤,彷彿仍殘留在指尖之上,難以磨滅。
思及青年一臉誠懇地說:「謝謝你的技術指導。」陸洐之真是……都不知誰該感謝誰好了。
隔天青年居然把一半房錢給了他,陸洐之雖訝,卻依然不動聲色地收下,還好裡頭沒給他包學費。
兩人的關係又恢復了往常,除了偶爾四目相對,裡頭都有點纏膩黏人的東西,彷如蜂蜜。
一天,陸洐之去專櫃買香水,他固定用Hugo Boss的其中一款,他對香氣並無偏執,純粹是因香水混用,會殘留在衣服上,最後整櫃子都是亂七八糟的味道。
至於用香水,很簡單,他抽菸,抽得很兇,紅萬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都高,不灑一點,掩不過去。
久而久之,Hugo Boss、Marlboro,便成了滲入他身體裡的一種印記。
他在專櫃上看到著名的CK One,這是款中性香,氣味清透,後味與他慣用的香水類似,卻不若那般奢糜。他停佇下來,取了香水紙試聞,年輕乾淨,很適合那人。
不過喬可南從不抹香水,或者說,他本身散發出來的味道,就足夠吸引人。
當晚,陸洐之作了一場極致淫靡的夢。
夢裡的那人猶如妖精化身,無一處不誘引著男人,陸洐之粗大的性具勃起,不帶猶豫地拉扯開青年的腿,一舉侵入。
那兒緊緻柔軟,食髓知味似地吸附著他,任其幹至深處,將黏膜狠狠搗開,陸洐之痛快淋漓,毫不留情,操得青年落下淚來,連連告饒:「饒了我……饒了我……」
在高潮之際,陸洐之醒了。
他一頭熱汗,下腹明顯濕漉,令他不可置信──他居然夢遺!
又不是十六、七歲的青春少男……
陸洐之洗了澡,換下褲子,狼狽取了菸,在陽台上抽,他沒料到,自己對青年的慾望,居然膨脹到了這種境界。
之後,他們又發生了一次性關係。
那次是自己引誘的,喬可南明顯就是個意志不堅的傢伙,動搖一下,便嗯嗯啊啊地應了。
陸洐之喜歡他這個樣子,坦白直接,他不肯為自己口交,他能理解,但仍動念欺負,就叫他幫忙用嘴戴套,喬可南不大願意,卻乖乖做了,還很認真,調整學習,現實裡的他比夢裡少了那般妖嬈,卻多了鮮活,教人愛不釋手。
陸洐之心想他真無法放他走了,治癒的物件還是得放入手心裡,成為自己的,才能安心。
他很直接就說:「我們交往吧。」當然,不會是一般的「交往」。
喬可南很聰明,問他:「交什麼?」
他說:「炮友。」
他是一開始就不打算談感情的,不論對象是誰都一樣,秉持了快三十年的原則,沒道理隨便破壞掉,他很喜歡喬可南,但不是愛。
即便是愛,有些東西,他不可能放得了。
他以為喬可南受過情傷,該能比他看得更開,沒料他居然……嫌他不乾淨。
偏偏對此,陸洐之無話可回,他定期有做身體檢查,但與他有過關係的人,太多太多,相比喬可南,他這兒確實是一本爛帳,厚度堪比辭典。
喬可南提及他前伴侶的事,說:「儘管不是他單方面的問題,不過……我就是挺不喜歡的,那種你上我我上他的關係。」
陸洐之反問:「你想我們談感情?」
問出這句話時,陸洐之心情很雜。
他既希望喬可南說不,又覺他說了不,自己會怎樣呢?
答案很快揭曉,喬可南搖頭當下,陸洐之隱約鬆了口氣。
他直覺跟喬可南牽扯得太深,會改變許多原先賴以為生、視作信仰的東西,就像在一個半路出家的佛教徒面前,飲酒吃肉,做盡誘惑之事,引導他往非計畫好的方向走。
那裡不是陸洐之想踏入的世界。
無奈,喬可南太吸引他。
吸引得他無法自控,擁抱那人的感覺太好,好得令他心知愚蠢,仍想誘引,在他算計以外的是喬可南居然真的雷打不動,陸洐之感覺自己像個在瞎子面前跳豔舞的女郎,哭笑不得。
說實話,喬可南不願,就算了吧,交友本就是你情我願,遑論炮友?
陸洐之緩下了對青年的慾望,轉而去找更與他志同道合的人,酒吧裡這樣的人不少,大夥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,與他搭訕的人多數條件良好,知情知趣,一夜過後,一拍兩散;喬可南看似大度,實際認真到了骨子裡,他別沾惹,對兩人都好。
然而看見喬可南與另一個溫秀青年,在酒吧裡親暱依偎,相互餵酒的畫面,什麼顧忌,通通被陸洐之拋到了腦後。
他只差沒上前搖青年肩膀,安掬樂的名聲不比他好多少,你能與他扯上關係,與我卻不能?
陸洐之難得灌起了酒,越看越撓心,連肺都快抓穿,好不容易夜深了,見喬可南把安掬樂送上車,沒一塊走,才把悶了一晚的氣給吐出。
他沒醉,純粹只是依循本能,想在另一個人吻過的地方,重新烙下自己的痕跡。
他甚至像隻發情的狗,討好地拚命蹭,「讓我做、我想做……」
「欸……」喬可南心軟,猶豫了會,終是讓他為所欲為。
陸洐之不喜歡太粗暴的做愛方式,這次卻把人綁住了,他隨身帶了KY,然而最終用自己射出的液體取代,做了潤滑。
這在以往從未發生,即便是最莽撞無知的年少時代,他都沒這麼做過,他甚至做了另一件失序行為──他在喬可南頸脖上咬出了痕跡,那麼堂而皇之,那麼理所當然。
他讓青年喊他哥哥,這是同志間的愛稱,他沒聽人喊過,卻很想聽喬可南這般喊他的音調。
結果比他想像中的還要美好。
兩人都射了,接吻的時候,喬可南漆黑的眼珠在車燈映照之下,像面鏡子,牢牢吸附著他的身影。
如此酣暢淋漓的性愛,無法說前所未有,但也很難取代,喬可南像是覺悟了,說:「我同意跟你打炮,但你不能跟別人,你要想跟別人這個……我們就切。」
陸洐之一愣,沒聽過炮友間還要遵守那一對一的規則,這和情侶交往有啥不同?
他單純好奇,反問:「你怎知道我有沒跟別人做?」
喬可南大略也明白這很難證實,索性道:「自由心證唄!要我說,別跟你扯上關係最好……」
他口氣一派天大不幸,陸洐之悻悻,掐了他的下身,冷聲問:「別跟我扯上關係……最好?」
「欸欸,別揉了別揉了,要硬了!」
…… |
|
|
|
|
|
|
|
|
※ 謝 謝 試
閱 ※ |
|